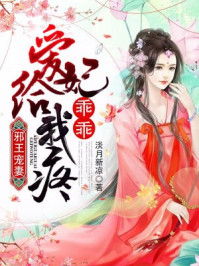房門發出的巨響聲,把展小白吓了一跳。
慌忙抓起話筒,就要召喚保安過來護駕,卻又及時醒悟,她現在可是把這破人給捏死了,不敢把她怎麼着。
膽怯消失,展小白拍案而起,黑葡萄般的雙眸惡狠狠盯着沈嶽,寒聲問:“我就是欺你太甚了,你能把我怎麼樣?”
“我”
沈嶽口結。
人家問的不錯,就是欺負他了,他能把她怎麼樣?
總不能因為這點破事,就不顧嫂子的安危,亡命天涯吧?
“破人,沒膽把我怎麼樣,那就給我乖乖的。哼。”
看沈嶽隻能叫花子咬牙窮發狠,展小白更加得意,蔑視地輕哼一聲,才坐下繼續邊吃零嘴邊工作。
破人就是破人,展總剛要把一顆牛肉幹填進嘴裡,他就提出了新的要求:“我要撒尿。”
人活着就得吃喝拉撒睡,很正常。
可這破人,就不會說要去洗手間嗎,非得說那麼粗鄙的話,誠心惡心正在吃東西的展總。
羞惱之下,展小白嬌聲冷叱:“不許!”
沈嶽面無表情的點頭:“好吧,那我就在這解決問題了。”
他在這站一下午了,早就積攢了大量的存貨。
人能忍住餓,卻憋不住尿。
“你”
展小白再怎麼刻意刁難他,也不能在這種事上做文章,隻好擺手:“去吧,去吧。”
沈嶽立即快步走向洗手間。
剛走沒幾步,卻被在展小白喝住:“站住,是誰讓你用這個的?去外面的公共洗手間。”
像展總這種長相清純的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潔癖,尤其在這方面,謝柔情都沒進去過,更何況沈嶽這個臭男人?
沈嶽也沒反駁,轉身出門。
“我呸。懶驢拉磨,不哼。”
輕呸了下,展小白重新開始工作。
饒是展總今天狀态出奇的好,可要想在短時間内,解決以往不好解決的難題,還是很讓她頭疼。
偏偏,就在她秀眉緊皺着絞盡腦汁時,某破人再次說話了:“我要撒尿。”
展小白擡頭,怒叱:“你不是剛去過嗎?”
沈嶽還是面無表情:“現在又想去了。”
“你、去吧,去吧。”
展小白實在拿不出為難他的理由,不耐煩的擺擺手,示意他自便。
七八分鐘後,盯着某個難題的展小白,腦海中剛有靈光乍現,要抓住什麼時,就被沈嶽再次打斷:“我要撒尿。”
差點抓住靈光的展小白,幾乎被氣瘋了,尖聲叫道:“沈嶽!你、你混蛋。”
“不讓我去,我就在這解決。”
沈嶽木木地回答,并作勢解腰帶。
展小白再傻,也能看出這厮是故意的了。
而且他的觀察能力超強,後兩次提出要去撒尿時,都在展小白即将抓捕到問題關鍵點時,及時打斷。
可她又沒任何的辦法。
她能在捏着沈嶽死穴時,可勁兒的打擊他,人家同樣能在被允許的範圍内,和她搗亂。
再怎麼苛刻的老闆,也不能不許保镖解決生理問題吧?
這種情況下,展小白哪兒還能安心工作,唯有推開筆記本,冷着臉的說:“快去快回,我們下班。”
按照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甲方沈嶽要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為乙方展小白提供保镖服務。
但展小白除了每月支付兩萬塊的月薪之外,還要負責沈嶽全部的衣食住行。
那麼這就證明,自從今晚開始,沈嶽就要搬到展小白家去住。
從小到大,除了父親外,展小白還沒和任何男人同居過,尤其沈嶽這種思想道德極其敗壞的破人。
可随時出現的職殺,卻又迫使她必須這樣做。
“放心,就你這副小帶魚身材,哪怕主動要求我侵.犯你,沒有十萬塊,我是萬萬不幹的。”
沈嶽仿佛展小白肚子裡的蛔蟲,知道她在想什麼,雙眼上翻看着電梯天花闆冷笑:“因此,你大可不必在包裡裝個剪刀。”
“去死!”
展小白小臉一紅,擡腳做了個要踢死他的動作,心中卻在奇怪:“我在休息室内裝剪刀,他是怎麼看到的?”
沈嶽又說話了:“進電梯後,你就左手牢牢抓着小包,右手放在拉鍊處。這個動作,擺明了就要随時掏東西的樣。哼,你真要有值得我犯罪的資本,一把剪刀也攔不住我的。”
展小白閉嘴,決定以後盡量不和這破人說話,不然非得被他活生生的氣死。
叮的一聲輕響,電梯門開了。
天已擦黑,除了保安部.門外,大部分員工早就下班回家了。
看到展總快步走出大廳後,今晚值班的王有盛,立即殷勤的跑過去,要像往常那樣幫她倒車。
别看展總開的是豪車,可倒車技術實在不怎麼樣,每次都需要人幫忙。
谄媚的對展總笑了下,王有盛又對沈嶽讨好的點頭示意。
現在全公司的人都已經知道,涉嫌把他頂頭大上司賣了個好價錢的沈嶽,非但沒被開除,還成了展總的專車司機。
能夠和這種牛人交好關系,肯定能給老王帶來天大好處的。
老王的讨好笑容,對沈嶽來說就像撥開濃霧的一束月光,心情好了許多。
從小包裡拿出車鑰匙,展小白剛要去*門,卻又遞給了沈嶽。
沈嶽不解:“什麼意思?”
展小白冷冷地說:“身為我的專車司機,難道還要我*?”
看在她言之有理的份上,沈嶽不好反駁,在王有盛羨慕的目光中,上車。
大老闆坐車時,一般都是坐在後面。
展小白卻坐在了副駕駛上,系好安全帶。
她實在不放心這厮的車技,為自身安全考慮,必要時可以指點一二。
可當她看到沈嶽動作娴熟的啟動車子後,有些小驚訝,忍不住問:“你以前開過這麼好的車?”
沈嶽笑了下,沒說話。
他雖然沒說話,展小白也能從他笑容中,看出濃濃地譏諷,仿佛在說:“百十萬的車子,又算什麼好車了?由此可見,你就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土鼈。”
被一個身穿地攤貨的破人暗諷是土鼈後,展小白小臉漲紅,剛要發怒,卻又找不到借口。
人家隻是笑了下而已,又沒指名道姓的罵她小土鼈。
經過一家飯館時,沈嶽輕點了下刹車,看向了展小白,意思顯而易見,想在這兒吃飯。
擡頭看着正前方的展小白,卻沒絲毫的反應。
無奈之下,沈嶽隻好繼續前行。
此後每經過一個飯館,他都會看下展小白。
展總也每次沒有任何反應。
經過第七家飯館後,沈嶽實在忍不住了:“展總,合同裡可說好,你要負責我的衣食住行。”
展小白無聲冷笑,反問:“我有說過不負責嗎?”
“那怎麼不去吃飯?”
“回家吃。”
展小白冷聲說:“我家有廚房。合同裡也沒說,我負責你的衣食住行,就要請你下館子吧?”
沈嶽一驚:“你做的飯菜,能吃嗎?”
展小白眉梢一挑,淡淡地說:“我有二級廚師證書。”
沈嶽盯着她看了半天,怎麼看,她都不像會做飯的樣子。
展小白也不理他,剛要閉眼休息下,小包裡的手機響了。
拿出手機看了眼來電顯示,接着又放了進去。
手機響了會,停止,但接着又響,如是者再三,沈嶽忍不住問:“你怎麼不接電話?”
“要你管。”
展小白沒好氣的呵斥了句,卻拿出手機,盯着屏幕呆愣片刻,接通了電話。
手機内傳來了一個溫和的男人聲音:“小白,你現在哪兒?”
“在公司。”
展小白睜着大眼說瞎話時,臉一點都不紅,語氣還很生硬。
男人再說話時的語氣,依舊溫和:“回家吧。”
“我已經睡了。”
聽她說出這句話後,沈嶽猜出是誰給她打電話了。
除了她父親之外,相信就沒哪個男人,能對她這般寬容了。
“回來吧,小白。”
男人低聲說:“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了。
簡簡單單的五個字,卻像一把刀那樣,狠狠刺在展小白心尖上,使她再也無法假裝堅強,情緒崩潰,嘶聲叫道:“不,不,我不回家!媽媽不要我了,你也不要我了,殺手要來殺我了。我、我現在好怕,特别特别的想媽媽。如果她還活着,多好?”
這兩天,她獨自承受的大恐懼,現在猶如沖破大堤的洪水那樣,瞬間把她淹沒,扔掉手機後雙手捂着臉,失聲痛哭起來。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展小白才抽噎着放下手,淚眼婆娑中,看到沈嶽遞來了兩張紙巾。
“我才不要你可憐我。”
展小白嘴裡這樣說着,卻一把搶過紙巾,擦着淚水恨恨地說:“别以為我不知道,你表面上憐憫,實則心中在罵我活該。”
沈嶽特無語。
她在精神崩潰後喊出那番話後,沈嶽才知道她已經沒有媽媽了,是個需要嶽哥這種鐵皿男兒舍命保護的可憐孩子可她現在的表現,又讓沈嶽覺得,她不被殺手刺殺,實在是沒有天理。
“回家。”
展小白把紙巾揉成一團,攥在手心裡,紅着眼睛看着前方:“南山路陽光領秀城十八号。”
半小時後,車子剛停在展家别墅大門口,鐵栅欄就緩緩移開,一個身穿黑色旗袍的三旬少婦,快步從鐵栅欄後走了出來。
借着明亮的門燈,沈嶽看向少婦的臉,眼睛一亮:“哇,好靓的嫂子。”
話音未落,就聽展小白冷冷地問:“把她送給你?”
作者公衆号:風中的陽光,老鐵們都來玩玩,有什麼話想對陽光說的都來看看,長評有獎,更有陽光自己的日常和一些想對大家說的心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