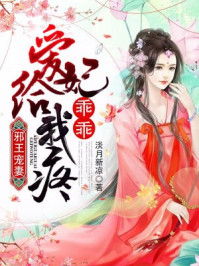被老錢洗腦後一心要幹番事業,又有了個還算可以的未婚妻後,沈嶽現在一心要做個良民。
要不然,在趙坤等人動作粗暴抓捕他回來時,他就翻臉了。
不知哪個坑爹的大爺,把讓任明明蒙羞的視頻上傳網絡,她現在有多麼的狂怒,趙坤等人又是什麼感受,包括謝柔情有必要那麼着急嗎等事,沈嶽統統沒放在心上。
反正他又沒真拍下教訓任明明的不雅視頻,更沒上傳網絡上,即便被坑爹的某人陷害,被抓進區分局後,相信也很快就能真相大白,就像前兩次來警局“做客”那樣,被主要領導恭送出門。
一點也不耽誤,傍晚陪同未婚妻回家陪老丈人過生日。
但他還是小看了任明明,對這件事的反應。
這和他并不知道任明明的真實身份有關。
直到任明明貌似瘋了的小母豹般破門而入,拿槍對準他腦門時,沈嶽還沒當回事,而是禮貌的警告她,别拿槍對着他,要不然他會不高興。
隻是沈嶽剛說出這句話,任明明就尖叫着扣下了扳機。
卧槽。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就在子彈出膛的電光火石間,沈嶽雙眼瞳孔驟然猛縮,腦袋仿佛被高速動車給撞上那樣,向後仰去。
槍口有火舌噴濺時,子彈幾乎是擦着沈嶽左耳激射而過。
然後,才是沉悶的槍聲。
“她真要斃了老子!”
躲開子彈的沈嶽勃然大怒,霍地擡頭的瞬間,右腳屈起,蹬在了任明明的小腹上,全力外踹。
也幸虧倆人是面對面站在一起的,沒有太多空間讓沈嶽起腳飛踹,隻能蹬。
如果給他足夠的飛踢空間,全力一腳踹在任明明身上後,鐵定是腸斷骨折的下場,而不是好像溜冰那樣,雙腳不動,整個人卻飛速向後滑去,重重碰在了牆上。
牆壁反彈回來的巨力,震得任明明直覺全身骨頭都碎了,眼前發黑,更想張嘴,哇的吐出一口鮮皿。
她忍住了。
在亂冒的金星有所消散後,徹底瘋狂的任明明沙啞笑着,再次舉槍,對着沈嶽接連扣下扳機。
多少年後,任明明在想起今天這一幕後,依舊會心有餘悸。
不是親眼所見,她是斷斷不會相信,被反铐在鐵椅子上的沈嶽,在這麼短的距離内,竟然能連續躲開她的兩發子彈。
“這,這還是個人嗎?”
任明明吓呆了,雙手抱着手槍,愣愣地看着沈嶽,張大的小嘴裡,估計能放進一個茄子
究竟過了多久,任明明才從極端不可思議中清醒了過來?
一秒鐘,還是一個世紀?
反正等她清醒過來時,明明被反手铐在鐵椅子上的沈嶽,已經站在了她面前。
她的手槍,已經到了沈嶽的手上,黑洞洞的槍口,頂在了她腦門上。
這不可怕。
可怕的是,沈嶽眼裡閃着讓她隻想吓昏過去的妖異光澤,就仿佛有個無形的惡魔,藏在他的眼裡,正無聲的咆哮着,試圖撲出來,把她撕成碎片!
沈嶽也确實有想把她撕成碎片的強烈沖動,不然他的呼吸,不會這樣沉重。
幸好,他還能控制住自己。
他還真不明白了,慢說那段坑爹的視頻,不是他發的,即便是,任明明又有什麼資格和權利,敢在他沒被推上法庭接受正義的審判之前,私下裡要斃了他?
這個把兩個大、奶、子藏着的臭女人,簡直太嚣張,太過分了!
還真把她自己當做是古代女王,想尼瑪的殺誰,就殺誰了?
她該慶幸,這是在華夏!
任明明終于怕了。
喪失理智的人知道怕了後,就是正在恢複該有的理智,認識到剛才的瘋狂,是多大的錯誤。
任明明小臉蒼白,全身顫抖的驚恐樣子,讓沈嶽徒增無比的快樂意思。
也可以說是邪惡。
仿佛被邪惡控制了的沈嶽,現在不想殺她,卻想用某種方式,來讓她付出沉重的代價。
至于這是在哪兒,對邪惡的沈嶽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他是這樣想的,也開始這樣做。
右手裡的手槍,用力頂着任明明的腦門,迫使她側臉貼在牆上,左手把她用紮住的短袖襯衣下擺,自腰帶内拽了出來。
接着,他那隻罪惡的手,就緊貼着她光滑平坦還在顫抖的小腹,迅速上身,把束*的黑色絲帶推到了上面,抓住一個,狠狠的擰。
他在這樣做時,任明明卻沒敢有任何的反抗。
隻因她能從沈嶽閃着妖異邪惡的眼神中,清晰意識到她真要反抗,他就會扣下扳機,把她腦袋打個透明窟窿。
但當那隻手,狠狠擰住左邊的球形體後,任明明還是扛不住劇痛,張嘴慘叫:“啊”
叫聲未落,通體黝黑的手槍槍管,直接頂在了她的嘴裡,讓她再也發不出絲毫的聲音。
“再敢叫喚一聲,老子就斃了你。”
好像變了個人那樣的沈嶽,拿出了手槍,也縮回了左手,語氣陰森的低聲喝道:“跪下。”
做錯事給人下跪求原諒,是古代常見的賠禮方式,流傳千古的将相和典故,不就是以廉頗給蔺相如給下跪,負荊請罪為結局嗎?
就算放在現代,也有人這樣做。
任明明當然不想這樣做,可又不得不遵從沈嶽的命令,隻因她現在怕的連靈魂都顫抖,完全無法控制自己,在他的話音剛落下,就屈膝跪倒在了地上。
沒有淚水,也沒任何的屈辱感,隻有滿心的恐懼。
“接下來要怎麼做,還需要我來教給你嗎?”
沈嶽淫淫的笑着,左手拉開了拉鍊手槍頂在了任明明的前額,往下一按。
嘴唇碰到某個發燙的東西後,任明明這才意識到,他讓她跪下,不是為了讓她賠罪,而是要給他
就在區分局的審訊室内。
審訊室外,還有很多随時沖進來的同事。
她當然會拒絕,緊閉着雙眼,緊閉着嘴,任由那個東西在她臉上來回的抽,甯死也不從。
“三,二,一。”
沈嶽倒計時的聲音,為什麼會沙啞了?
而且,邪氣更盛,帶着要毀滅整個世界的邪惡。
難道說,現在的沈嶽,已經不是他本人了,而是被某個可怕的惡靈附體?
誰知道呢。
反正無論他是誰,任明明都不會答應他卑鄙的淫邪要求。
她繼續搖頭砰!
槍聲響起,就在任明明耳邊,吓得她張嘴剛要尖叫時,嘴裡多了個東西。
一個念頭,閃電般浮上了任明明的腦海:“我給他吃了。”
沈嶽深吸一口氣,抓住她的頭發,剛要有所動作時,屁股上就被人踢了一腳。
接着,有個脆生生的聲音傳來:“沈嶽,你這是要給我惹禍嗎!現在我以老婆大人的身份,命令你放開任隊!不然,别怪本老婆大人翻臉無情!”
沈嶽霍然回頭,看去。
展小白破門而入時發出的聲音,已經夠響了,他竟然沒聽到。
直到看到他竟然拿槍逼着任明明下跪的展小白,大吃一驚沖過來,擡腳踢在他屁股上後,沈嶽蓦然回頭看來時,雙眼中吓人的邪惡,就像被電光趕走的黑暗那樣,迅速消失在瞳孔深處。
審訊室裡的沒窗戶的,隻有一扇鐵門。
任明明沖進來時,也沒開燈,所以哪怕是在大白天,光線也有些暗。
任明明能看到沈嶽可怕的眼神,那是因為她的眼睛,已經适應了當前的光線。
剛沖進來的展小白,還沒适應當前環境,休說沒看到他雙眼裡迅速隐沒的邪惡了,就連跪在地上的任明明,嘴裡吃着個什麼東西,都沒注意到。
展小白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沈嶽逼着任明明下跪的那把槍上了。
放在以前,展小白看到這種事後,肯定會避之不及,或者幹脆搬個小馬紮坐在旁邊,喝着大茶看戲。
現在不行啊。
她真心需要沈嶽來賣命,當然不能眼睜睜看着他亂來,必須拿出老婆大人該有的淩厲,來訓斥這個家夥,當前這動作,純屬自己找死呢。
卧槽。
我是誰?
我這是在哪兒?
我這是在幹什麼?
看到滿臉怒容的老婆大人後,沈嶽用力眨了下眼,腦海中攸地浮上三連問的瞬間,就找到了答案。
我是沈嶽。
我這是在區分局的審訊室内。
我這是在強迫任明明給我吃,隻因她竟然敢對老子開槍。
尼瑪,就算她是個正道該死的,可我也不能在這種地方,讓她給我如此服務啊。
尤其老婆大人還在場,這不是要毀滅幸福下半生的節奏嗎?
謝天謝地,老婆大人貌似沒有注意到我那玩意在哪兒
心思電轉間,沈嶽借着半轉身的機會,左手在胯、下抹了下,某個東西就乖乖歸位,褲子拉鍊也被拉上,尴尬的笑着:“老婆大人,這是不能怪我。是她想槍殺我,我隻是被迫自衛反抗罷了。”
“那你也不能用這種有損任隊尊嚴的方式啊?哈,你還敢頂嘴,信不信我馬上告你昨晚強女幹了我?這可是在警局,外面就有大批的警察,隻要本老婆一聲令下,他們就會沖進來,把你就地正法。”
看到沈嶽還有要狡辯的趨勢,展小白有些生氣,擡手擰住了他耳朵,銀牙緊咬,一雙大眼睛惡狠狠的看着他,貌似要吃人。
沈嶽趕緊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狀。
“給我滾回椅子上,不然别怪我不顧夫妻情分,讓你把牢底坐穿!”
展小白低聲呵斥着,一把奪過手槍,随手扔在了牆角,這才松開他的耳朵,彎腰伸手攙住徹底傻掉的任明明,關心的問:“任隊,你沒事吧?這都怪我家教不嚴、不對,是禦下不嚴,冒犯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