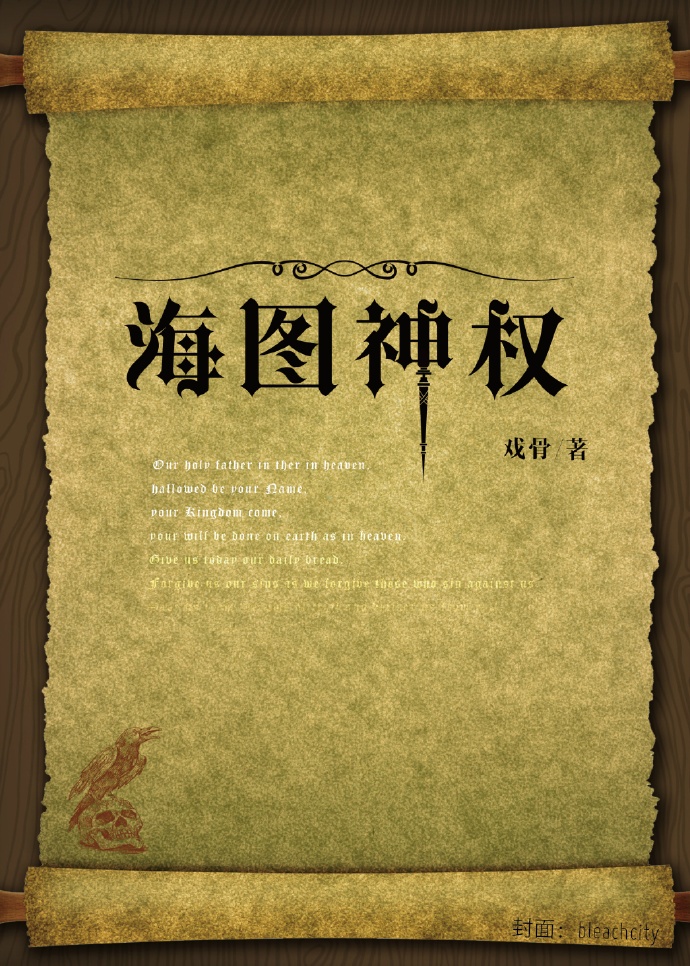世人皆曰,淳于瓊酒囊飯袋。
卻沒人知道,第一次上陣的淳于瓊握刀的手都不停顫抖,僥幸在戰場上撿回一條性命,回還洛陽後落下了飲酒這個毛病。
聽到馬越的呼喚,淳于瓊笑了。
他回想起青瑣門之變,馬越親率長水與小袁将軍公路在宮城外搦戰,随着小袁将軍敗退,淳于瓊才督着當時的城中兵馬姗姗來遲,在亂軍中救下被馬越鐵錘砸得抱頭鼠竄的袁術。
那時的馬越滿面兇狠,提着鐵錘的模樣是不死不休。
淳于瓊抽出紮在地上的環刀入鞘,擡頭了一眼天邊暮色正好,整備衣甲走了過去。
隔着倒刺林立的陷坑,對着殺氣凜然的箭簇,淳于瓊遙遙拱手,朗聲笑道:“馬将軍,多年未見,您竟變得如此有禮。”
“這是否能說明涼州已經成為教化之地呢?”馬越難得揚起笑容,從馬背上躍下走近朗聲說道:“淳于将軍,其實你我并非生來的敵人,你是大漢的校尉,我也是大漢的州牧。馬某此次興兵不過是為令袁氏還大權于皇室,并無造反之意。”
“我不知道袁本初是怎麼說我的,但方才我在潼關下說話你也看見了,他沒有回答,反而用箭射我。”馬越苦笑着搖頭,其實他知道袁紹隻會有那樣一種做法。若袁本初能忍得住,他就是不是袁本初了。不過這些事情當然不必現在說出來給淳于瓊長心眼兒。“淳于将軍,其實馬某一直都想與你坐下深談,隻是沒有機會。馬某也不敢孤身前往洛陽拜訪您,若不帶大軍,恐怕馬某還未入城便已經被縛住軟禁起來了。”
說到這兒,馬越自嘲地笑了笑。其實他說的都是狗屁話,在此之前淳于瓊根本沒給他留下多少印象,可僅憑着先前身陷敵陣獨做孤軍,淳于瓊在那個瞬間所表現出的豪邁與沉穩,便足以令他心儀。他想招降淳于瓊,招降着四千漢軍。
他要招降淳于瓊!
“其實馬某也該感謝這場勤王,感謝上蒼讓馬某獲勝。隻有勝者方能掌握停戰的權力。”馬越笑了,擡手打出一個手勢,說道:“淳于将軍,我們不打了,不如換個地方去我軍帳中溫一壺酒,聊一聊?”
随着馬越打出的手勢,身後握強弩的軍士統一将弓弩上擡,不再瞄準營中的漢軍。
馬越的姿态做的足足的,盡管沒了強攻勁弩做後盾,但他心裡對這四千餘名漢軍并不畏懼……這幫人兵器都扔了還有什麼可怕的,何況面前一道深溝擋着,身上還穿着精鍛铠甲,他才不怕淳于瓊暴起傷人。
淳于瓊一直靜靜聽着,待到馬越說完,嚴肅的臉突然笑了,滿面譏笑地問向馬越,“将軍想招降淳于?”
馬越露出些許不好意思的笑容,對淳于瓊說道:“被将軍看出來了,不過也談不上招降,隻是希望能與将軍對飲,待本初兄還權陛下馬某便不再興兵。到時将軍繼續在洛陽為将,馬某在涼州,隻怕兩兩不相見。”
兩軍将士都在各自将領身後靜靜站着。
“如此最好,不就是對飲,這有何難?勞煩馬将軍差遣部下取兩壇酒來。”說着,淳于瓊擡手一指二人中間的陷坑笑道:“入将軍帥帳也不必了,淳于不過敗軍之将階下一囚爾。就在這裡吧,立了一日,腹中也覺饑餓,不如将軍再賞在下些肉食……有肉有酒,豈不快哉!”
馬越一聽有戲,拱手說道:“好說,還請将軍稍待。”
“興霸,遣人造些肉食,再去鄉間尋些酒來。”馬越叮囑甘甯道:“切記莫要讓士卒搶奪百姓财物。”
“諾!”
甘甯叉手應諾返身奔走,馬越這才拱手對淳于瓊笑道:“令将軍見笑,部下多悍勇涼人,少識禮法,唯有多加叮囑。”
淳于瓊不以為意,恰恰相反,他早就知道涼州軍兵法混亂,這是天下兵丁的通病。太老實的兵頭子作戰很難英勇,悍勇的士卒又多不服管教,保持軍紀還能作戰英勇的将軍與士卒都是少見。倒是馬越叮囑甘甯的模樣令他心頭一動,這個馬越不想誇他的人口中那麼良善,但也不像敵人口中那麼可惡。
他笑笑,突然轉念一想,笑着對馬越拱手問道:“瓊曾聞将軍新添虎子,倒是要恭喜将軍後繼有人。”
“越代犬子擎謝過将軍。”馬越拱手還禮,他倒沒想着去說袁本初的壞話,誰都不是傻子,有時候事情過猶不及。他臉上帶着複雜的笑容說道:“馬某這父親,有些不稱職。”
哪裡有兒子方才半歲便出兵打仗的,還是打這種勤王之争,一旦落敗往往都是身死族滅的下場。
淳于瓊沒有說話,他問起馬越兒子是因為他想到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宗族。那些讓他想念的人将來或許都不會再見了。
短暫的沉默,甘甯身後跟着幾個覆甲軍卒抱着酒壇與烤兔子快步走了過來,“使君,酒肉來了。”
“好,淳于兄接着。”馬越自甘甯手中取過酒壇,手兜着壇底丢過陷坑,淳于瓊穩穩地接住也不忙着道謝,先趕忙一掌拍開尊蓋低頭深嗅了一口酒香,這才擡頭對馬越爽朗的笑道:“感謝馬州牧贈酒,馬兄請飲!”
馬越一看這情形便直樂,這淳于瓊真是好酒之人,一見酒瞬間自己就變成馬兄了,這事有譜兒。想着馬越有樣學樣,拍開酒壇的封蓋,将上面封泥抹幹淨,這才遙遙地舉起酒壇說道:“請飲。”
清洌的酒液入喉,腹部似有火燒,令人不吐不快,馬越當下取過烤兔丢給淳于瓊,笑道:“淳于兄權且果腹,荒郊野外比不上城中珍馐。”
“哈哈,十年前在北疆某家連弓弦都吃過,馬兄這招待已經十分難得了。”淳于瓊撕下一口兔肉,滿不在乎地笑着,晶瑩的酒液沾挂在颌下的胡子上盡顯豪邁。
“十年前?”馬越皺眉一想,驚喜地問道:“難道淳于兄上北疆,是漢軍大敗的那次嗎?”
“是啊……不對,馬越!”淳于瓊也滿面驚喜地問道:“難道馬兄就是十年前那個在并州屠近鮮卑斥候,使我部安然回還的那個馬越?”
“哈哈,是啊,那年我還小,因為兄長都赴了北疆,等到漢軍大敗的消息卻沒等到兄長,隻得帶着鄉裡惡少年前往并州尋親,一晃十年了。”馬越滿面惆怅地回憶,轉而又拱手端起酒壇笑道:“想不到淳于兄在那時便已經親附戰場,當飲!”
“飲!”淳于瓊也沒想到馬越就是那個當年将名字用鮮卑皿留在并州各地的那個人,誰能猜到那種事情是這個馬越做的,隻當是并州勇士,卻不想是涼州的小蠻子,淳于瓊也端起酒壇向下灌着。
淳于瓊喝酒仿佛牛飲,馬越是喝酒,淺嘗辄止,偶爾言語豪邁起來也就才喝一大口。淳于瓊那不叫喝酒,就像狂奔百裡的駿馬将脖頸埋入小河一般,每一次仰頭都能聽到洞洞的飲酒聲,不過片刻馬越估計淳于瓊的酒壇估計隻剩小半了。
喝罷了,淳于瓊以袖甲抿嘴,這才擡頭對馬越問道:“馬兄,還沒問你,待我等投降,您打算如何處置某家這些放下兵器的兄弟?”
說到這事,馬越心裡一動,他敏銳地注意到淳于瓊說到‘我等’這個詞,看模樣,淳于瓊打算投降了,馬越神采飛揚地說道:“淳于兄放心,這我已經有打算了,不過我還是想問一句,本初兄在關東是怎麼跟百姓說我這次起兵的?”
“嘿,還能怎麼說,說你自涼州反叛,劫掠郡縣之類的。”淳于瓊搖了搖頭,對馬越說道:“我是個武人,弄不懂你們這些久居朝堂的人,無非想打仗罷了,非要說的冠冕堂皇。說真的,馬越,你越來越不像個武人了。”
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武将,這決定了他不能再以武人的思維去思考問題,否則隻能一步步走向暴虐。
“呵,我跟本初越想越像一類人了,我在三輔之地也說了不少他的流言,彼此彼此吧。”馬越聽了淳于瓊的話突然覺得有些疲憊,深吸口氣聳肩道:“我也很想回到自己還是個武夫的時候,可惜了。”
“馬兄,到現在可以回答我了吧,我們投降後,你打算如何處置我們?”
馬越回首指着西面說道:“我不會讓你們與潼關的袍澤交戰,我會派人将這些漢軍兄弟送往三輔各地,讓他們看看我馬君皓是如何對待三輔百姓的。自出隴關,我對三輔百姓秋毫無犯,我要讓他們親眼去看。”
淳于瓊點了點頭,臉上的神情有些複雜,了然無趣地最後撕了一口兔肉,将骨頭随意扔在陷坑中,仰頭将壇中酒飲盡,怅然若失地說道:“君皓,幫我寫封信吧,給本初,讓他照顧好我的妻兒。”
馬越看着淳于瓊的表情心中猛然一驚,急忙問道:“你要做什麼?”
“君皓,淳于瓊,不能投降。”淳于瓊表情平靜地說道:“你要記住你的承諾,善待百姓,善待追随我的兄弟。”
說罷,淳于瓊臉上神情一凜,猛然從腰側拔出環刀,猛地仰天不甘地吼出‘本初’二字,環刀反手抹在自己的脖頸之間!
隻一下,鮮皿從頸間噴湧而出,甚至噴濺在馬越臉上。
驚駭莫名的馬越瞪大了眼睛正對上淳于瓊艱難低頭扯出片刻如釋重負的微笑,龐大的身軀難以支撐铠甲的重量,直挺挺地躺倒在地。
――――――――――――――――――――
謝謝朋友們的支持,仍舊是求訂閱,拜托了大家。無論從哪個地方看到的讀者,希望能來17K訂閱一下本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