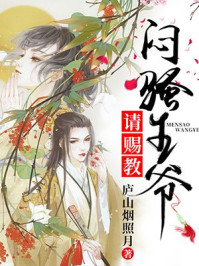劉煊宸和杜子彬沒喝到半盞茶的功夫,雲映綠随着小丫環走了出來。
“太醫,你診出王爺的病嗎?”齊王妃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捏着帕子的兩隻手輕顫着。
雲映綠擡起眼,如星辰般的瞳眸中帶着幾份羞慚,“齊王妃,我從醫也有幾年了,見過複雜的病患無數,但誰都沒有齊王的病這麼特殊,我從右手換到左手,在心中把所能考慮的都考慮過,還是無法給你一個确切的答案。王爺脈象微弱,病症深厚,但又隐隐有一股真氣含在其中,若這股真氣戰得過病氣,說不定就有奇迹發生在齊王身上。”
齊王妃好半天才把雲映綠這一番話琢磨懂了,她歡喜地問道:“太醫是說齊王這病興許有救?”
“奇迹無所不在,包括醫學,這是連神仙都難以猜測的。”雲映綠很認真地回道。
“皇上,這位太醫真是深得臣妾歡喜,來呀,看賞。”齊王妃激動得象手足無措,“皇上,日後臣妾能不能常麻煩太醫常到王府中替王爺把把脈、開個方子調理調理身子?”
劉煊宸意味深長地閉了閉眼,“當然,皇嫂想到雲太醫時,雲太醫會随叫随到。雲太醫,還不謝王妃的賞賜。”
小丫環捧着個盆子,上面罩着個羅帕,齊王妃掀開,露出兩塊上好的玉佩。
雲映綠不習慣“賞”這個詞,她所做的一切向來是勞動所得,這一“賞”象有點施舍的成份,令人心中不舒服。
她隻是遲疑了下,杜子彬不動聲色從後面推了她一把,她剛好走到齊王妃面前,無奈接過那對玉佩,“謝謝!”她禮貌地說道,回轉身就瞪了杜子彬一眼。
杜子彬面無表情地避開她的眼神。
劉煊宸又和齊王妃聊了幾句家常,然後三人告辭,齊王妃直到看不見馬車的影子,才轉身回府。
此時,天色漸灰,雲層很密。夕陽的光線漸漸被四籠的暮色遮掩。
馬車内慢慢暗了下來,看不清三人的表情。
“雲太醫,你沒什麼和朕說的嗎?”劉煊宸忽然開口道。
良久。
雲映綠擡起頭,手無助地在空中擺了擺,象要抓住什麼來按捺心底的情緒,不慎指尖擦到了劉煊宸的臉腮,他一怔,突地握住了她的手,一手的冷汗。
“怎麼?”他的聲音一下子嚴肅起來。
杜子彬神經一下子也緊繃起來。
“那是個死脈,雖然仍有體溫,但氣息已無,應是剛死不久。”雲映綠穩定了下心神,鎮定地說道,“我怕自己診斷錯誤,特别換了手,仍然是那種脈象。那不是齊王,我細看了下骨節,那應是一個已年過半百之人的手臂,而且是做粗活的人,掌心密布着硬繭,指甲破裂,滿布污垢。”
“你有沒吓到?”劉煊宸一點也不驚訝她的話,他更關心的是雲映綠的感覺。
雲映綠歎了口氣,“我又不是第一次見死人,以前實習的時候,我還親自解剖過屍體呢!但還是有一點吃驚,為一個剛死的人診脈,我到是第一次。”
“你的謊言說得蠻溜嗎!”杜子彬在黑暗中哼了一聲,“齊王妃都被你的話說服了,還對你心生好感。”
“我沒說謊。每個人身上本來就有好細胞與壞細胞,一旦壞細胞打敗了好細胞,人就要生病。但如果人自身的免疫抗體敵得過壞細胞,人就會很健康。”雲映綠不服氣的反駁。
“巧言令色。”杜子彬閉上眼,心中對雲映綠在齊王府鎮定自若現是大吃一驚。這丫頭并不是處處笨!
“你做得很好,你說的這一番話,正巧是王妃想聽到的。今天,朕突然闖進齊王府,他們沒來得及準備,情急之下怕是打死了一個傭仆代替。”劉煊宸陰寒地傾傾嘴角,“朕今日算是确定了心中的猜測,杜卿,這算不算是咱們君臣今天收獲的一個奇迹?”
“是的,皇上,确是一個奇迹。微臣一見着小王子,心中就驚了半截,一個身不能動、口不能言的男人,是無法生兒育女的。皇上,如此推算,齊王五年之前,怕就已痊愈了?”杜子彬說道。
“杜卿聰明,”劉煊宸贊賞地點點頭,“朕從登基那天起,就一直注意着齊王府,飛王子不是關健,他是齊王沒病之前,王妃懷上的。真正的關健是王妃的前言不搭後語,王府中處處透着詭異,什麼有異味啊,什麼王爺不願見人啊!一個口不能言的人怎麼表達自己的意思?”
“還有床前的布鞋,錦簾後站着的男人。”雲映綠插話道,“一個癱瘓在床的人是不需要鞋的,那個人躲在簾子後,一定是見不得别人的人。”
“皇上,”杜子彬握了握拳,脫口說道,“以後請不要再讓雲太醫身處那樣的險境了,她……手無寸鐵,又無縛雞之力,那樣太危險了。”
劉煊宸眯細了眼,神情複雜地抿着唇,沒有作聲。
“能有什麼危險,我就一個看病的,對别人能有什麼影響,你想太多了。”雲映綠不解地眨眨眼。
杜子彬歎氣,剛剛還誇她呢,現在呆勁又上來了。她現在不知道自己已經屬于齊王要滅口的人之一嗎?
“朕尋思着齊王應是這兩年才痊愈的,不然前幾年為何沒有動靜的?宮中有人做他的内應,這人身份還不低,朕真要好好琢磨琢磨。”劉煊宸避開了杜子彬的問話,繼續剛才的話題。
“是哪位太醫有這麼大的能耐?”杜子彬蹙起了眉。
“解鈴還需系鈴人。”劉煊宸幽幽地吐了口氣。
杜子彬愕然地擡起頭,“皇上,那人不是死去好多年了嗎?”
“雲太醫不是說過嗎?奇迹無所不在,包括起死回生。”劉煊宸勾起嘴角。
“劉皇上,奇迹不包括起死回生,醫學上目前沒有這樣的先例。”雲映綠特地解釋道。
“哈哈,侍衛,來,撩起車簾,讓朕吹吹風,今兒事情錯綜複雜,朕頭昏昏的。”
侍衛把馬車緩緩停在路邊,跳下車,卷起車廂的兩面簾子,溫涼的夜風徐徐襲來,劉煊宸舒适地半躺着,轉身看向點起一盞盞燈籠的店鋪。
燈籠如星河,街人如潮水,好一幅熱鬧非凡的勝景。
“這是朕的江山,朕好不容易才建成這樣的繁華和安甯,朕怎舍得讓那些狂妄之徒來毀壞,不,朕不會讓他們得逞的。”
劉煊宸絮絮念叨,心中并無懼意,隻覺好笑和悲哀。
杜子彬敬佩地瞟了眼劉煊宸,警覺地巡視着四周,皇上雖身着便服,但剛從齊王府出來,他怕會被有心人算計。
雲映綠隻當是坐三輪車逛夜市,惬意得很,她傾身趴在車廂邊,興奮地張望着一家家店鋪。
忽然間,她感覺到腦後一陣冷風襲來,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見劉煊宸的笑容陡然寒凝,閃電般出手,抱起雲映綠,身子輕靈如乳燕,躍出馬車,在地上滴溜溜轉了個圈,穩穩地站定。
杜子彬驚得瞠目結舌。
一支細巧的袖箭晃悠悠地釘在雲映綠先前的座位之上。
侍衛們紛紛飛速下馬,撥出劍瞪向四周。街市喧鬧依舊,人人臉色平靜,沒有一點點異常。
“好大的膽子,敢動朕的人。”劉煊宸震怒之下,大喊一聲,“禁衛軍呢?朕不開口下旨,你們就真的不動了嗎?”
嘩啦啦聲響,原來在周圍的人流中還隐藏着幾十名内宮的禁衛軍。他們為了不讓劉煊宸的身份太顯露,隻是遠遠地尾随着。
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而且這目标不是沖着皇上,而是沖着皇上身邊的雲太醫,他們一時反應不過來,就沒現身。
劉煊宸這一喝聲,禁衛軍現身,街市上一片混亂,但把附近的屋頂、樹梢和店鋪都搜了個遍,也沒搜出個眉目來。
“皇上,這人可能本意是吓唬下雲太醫,并不是真的想傷害她。人應早已逃遠了。”禁衛軍頭領拱手禀道。
“你到說得輕巧,吓唬?若那箭真的刺中了雲太醫,你能用命抵嗎?”
“微臣失職,請聖上治罪。”
雲映綠哪裡見過這種陣式,腿軟得站都站不住,隻得攀在劉煊宸的手臂上,忍不住的渾身輕顫。
“劉皇上,說不定這是個孩子的惡作劇。”她好半天才恢複了正常,長睫撲閃撲閃,自我解嘲道。
沒人回應她的話。
“你們繼續留着這裡搜查,朕把雲太醫帶回宮,看有沒哪裡傷着。”劉煊宸的眉心凝成幾道深深的印痕。
雲映綠忙站直了身子,“劉皇上,我就是醫生,我确定我沒傷着。天色這麼晚,這裡離我家不遠,我直接回家好了。”
劉煊宸的眉峰還是不能展開,“朕怎麼能放心呢,若是那兇手再尋到你府上,有個意外,朕不在你身邊,如何是好?”
“劉皇上,我好象還沒那麼出名,也沒和什麼有結仇。”雲映綠婉轉地說道,“我今天連招呼也沒和爹娘打,就直接進了宮。這會還不回去,我爹娘不知擔心成什麼樣呢!”
劉煊宸眯起眼瞅了她好一會,“那好吧,朕送你回家,然後留兩個侍衛保護你。從明日起,你和你爹娘說一聲,搬進皇宮住一陣子。不準抗旨,朕對你已經讓步很多了。”
雲映綠硬生生地把欲出口的抗議咽下,無奈地低下頭。
“杜大人,你也一并上車吧!”劉煊宸沖着一直沉思不語、臉色嚴肅的杜子彬說道。
杜子彬沉重地點了點頭。
一隊禁衛軍護着馬車,浩浩蕩蕩往雲府駛去。
雲府大門前,竹青已經把脖子都仰酸了,一看見有馬車過來,喜不疊地跑過來,看到雲映綠由人扶下馬車,一句“小姐”被跟在後面的一個威儀的男人和杜子彬給吓得咽了回去。
老天,還有官兵呢!小姐犯法了嗎?
“這就是我家。”雲映綠扶扶醫帽,指指身後高大的豪宅,客氣地說,“你要進來喝杯茶嗎?”
劉煊宸掃視了一下夜色中隐約可見的亭台樓閣,沒想到雲映綠的家境這般優裕,難怪對錢财看得那麼輕,他搖了搖頭,“下次吧!你好生歇息!”他拍拍雲映綠的肩,對身後的兩個侍衛使了下眼色,兩個侍衛瞬即消失在夜色中,怕是攀上雲府中某棵樹,藏着去了。
“那再見!”雲映綠乖巧地退到牆角,讓馬車先通過。
“不,我等你進去,再走。”劉煊宸怕驚着雲府的人,自動把“朕”改成了“我”。
雲映綠笑笑,點點頭,轉身進去了。
雲府的大門徐徐合上。
劉煊宸怔了會,擡腳上馬車,見到杜子彬還立在路邊,問道:“杜大人,你不上車嗎?”
杜子彬恭敬地上前拱着手,“皇上,臣也已經到家了。”
“呃?”劉煊宸訝異地揚了下眉尾,“你和雲太醫住一起?”
“不,微臣和她是鄰居。”杜子彬不敢隐瞞,指指雲府隔壁的另一座幽靜的庭院。
“可是你不是對朕說你不認識雲太醫嗎?”
杜子彬窘迫地低下頭,“微臣那時……有難言之隐。”
“你也有難言之隐呀,找雲太醫看看不就行了。”
“微臣這難言之隐,雲太醫看不好。”杜子彬臉不禁脹得通紅。
劉煊宸深究地凝視着他,好半晌才點了下頭,“那好吧,既然杜卿與雲太醫住隔壁,雲太醫的安全,朕就放心了。”
說完,他放下車簾,馬車駛向夜色之中。
一路之上,劉煊宸一直在想,能讓杜子彬難言之隐的東東到底是什麼呢?
而站在路邊的杜子彬,平生第一次陷進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